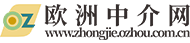许多年前,老丁刚上阿里时,狮泉河整个儿就是一片红柳滩。连队战士出去放羊,得用棍子缠一块红布,高高举起,以遥相呼应,不然,谁去哪里了,很难知道。整个狮泉河最高的建筑,就是连队的哨楼,两层。连队盖的房子全是土坯房。狮泉河周围的沙土没有黏性,战士们就把牛屎马粪装在麻袋里,在河水里把粪漂走,留下草渣,再把草渣与白石灰和在一起抹墙。抹出的白墙引得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全来参观,说这真是不得了哇,能住上这样的房子,就是神仙了。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现在,无论多么荒僻的地方也挡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击。现在的阿里,已几乎有了现代社会所有的一切。
无论在什么地方,老丁的心一直偏着阿里。他说:“我后来在新疆工作,但由于在阿里待得太久了,心里总记挂着那儿。每当看到火车装满了东西,我就想,这一车东西要是给阿里就好了。”
老丁的话,让人确信阿里的确就是他的家。虽然那里的极端艰苦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,可儿不嫌母丑,老丁对阿里这个家的情感一直非常深。
他告诉我,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,阿里官兵住的还是泥巴土块垒起的地窝子,睡的是下面垫羊粪、上面抹泥巴的土炕,不通电话,不通公路,给养物资靠牦牛、羊群驮运,吃新鲜蔬菜比吃山珍还难。他最后有些惋惜地说:“可惜你们现在吃不上用羊群驮到哨卡的食品了。无论大米、面粉,还是白糖、酱油,无一例外地都带有一股呛鼻的羊膻味、尿臊气。那风味,真是独特。”
那种独特的风味,可能只有那个独特时期的边防官兵可以品尝了。
那年边防建设的序幕拉开后,老丁高兴得几夜合不上眼。他当时任县人武部政委。施工大军还没有上山,他就带着战友们干开了。他整天泡在工地上,每天一干就是十四五个小时。高原施工,付出的体力要比山下多十几倍。
有一次天快黑时,别人已经收工,他想把最后一点土方挖完,没想到干着干着就晕倒了。这是很危险的高原晕厥。当时周围已没有一个人,幸好一位上山送物资的汽车司机发现了他,才把他救醒。司机以为老丁是个老兵,就说:“老伙计,你都成老兵了,家里一定还有老小,你该悠着一点儿。你想想,要不是碰上我,你就报销了。”
“没事的,我命大,这不就碰着你了吗。阿里高原施工期短,大家都和我一样,能多干点就多干点,都怕把工期给耽误了。”
“我得把你的事给你们政委讲一讲,你这样没死没活地干,至少也该立个功。”
“那倒用不着,比我辛苦的人多的是,就是该立功了,政委也知道的。”
但这位司机还是执意要找政委。搞得老丁只好告诉他:“我就是政委。”
有一次,他送新兵上山,一趟差点儿死了三次。
四月天,江南已经热起来,新疆叶城也有了暑气。新兵们初上高原,觉得好玩,一出叶城,就歌声不断,伸着脖子嗷嗷地一路唱歌。
老丁很感动,忍不住也随着新兵们吼起来。然后,他摸了摸头发稀疏的脑袋,感叹地对同车的干部说:“当年我也是唱着歌上山的。20多年了,一茬接一茬的年轻人把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了高原上,才使今天的阿里边防牢不可摧。可惜我年纪大了,不知道还能在这里干多久。把阿里从我的心里抽掉,我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寄托了。”
歌声不知不觉变弱,最后新兵们默然了。往外一看,已到库地达坂的脚下。高原反应开始折磨这些新兵们,几小时前还嗷嗷叫的战士这时正趴在后车挡板上哇哇呕吐。有些新兵因为难受,甚至哭起来。
老丁让车队停下,稍事休息,让战士们服用一些抗高原反应的药物。然后,他对战士们说:“上阿里的路,是勇敢者的路,是英雄之路。我们难道还能被喀喇昆仑吓退吗?我们就是把五脏六腑吐出来,也要上到阿里高原去。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?”
新兵们一声高吼:“有!”
“继续前进!”老丁命令车队。
冬去春来,积雪消融,山岩犹如豆腐渣,稍有震动,便会引起垮塌。为保证安全,老丁把车辆编队做了调整,把一辆拉物资的卡车和自己的车排在了前头探路。
车队艰难地爬上了库地达坂。
突然,老丁听见了一声冰河断裂的声音。他猛地对身边的司机大吼了一声:“停车!”汽车刚一个急刹停稳,就看见积雪崩塌,从山顶轰隆隆呼啸而来,狂泻在了车前。他感到眼前一黑,车被积雪埋住了。
后面的新兵赶快跳下来,用铁锹和手从雪中掏挖自己的政委。待把老丁掏出来,他已憋得呼吸急促,脸色青紫。
如果没有及时停车,再往前开一点,就处于雪崩中心,那就危险了。他大喘了几口气,拍打着皮帽子上的雪说:“真悬,都摸着阎王爷的鼻梁子了。”一句话说得惊魂未定的新兵们笑了起来。
折腾了大半天,终于把道路疏通。他让大家赶快往前闯。车队刚过完,一大块坚冰就砸了下来。新兵们说,政委是“天眼神耳”。老丁半开玩笑地说:“昆仑大学只收学生,但没有合格毕业之说。我和大家一样,都是这大学的学生,后面的考验还多着哩。”
接下来是从红柳滩到多玛。阿里军人有句口头禅:“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红柳滩到多玛。”他担心把新兵吓坏了,又补充了一句:我们阿里军人还有句口头禅,“东风吹,战鼓擂,阿里军人他怕谁。”算是给新兵们壮了胆。
从红柳滩到多玛360公里,海拔全在4500米以上。很多地方寸草不生,绝大多数道路艰险坎坷。当时正赶上冰河涨水,河水漫溢,到处是水洼和泥泞。车一开进水里,就辨不出路在何方了。这时车千万不能乱闯,稍有偏差,车子都可能滑下路基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老丁在阿里跑久了,对路线已熟若手纹。他心一横,牙一咬,脱去棉裤跳进齐腰深的冰水里,为汽车引路。12台车,老丁导引了12趟,花了8个小时。车辆全部脱离险境之后,他却因劳累和寒冷,一头栽进了冰水里。战士们把他捞进驾驶室,换了衣服,他还没有苏醒过来。此后半年多的时光里,他的双腿痛得没地方搁。那次造成的静脉曲张,必然要伴随他一生了。
他在讲起那次死亡体验时却是笑着的,甚至把失去知觉的感觉描述得很美妙。他说:“进入冰水以后,别的啥感觉都没有,唯一的感觉就是牙疼,那种疼特别难以忍受。桌面大的冰块一次又一次撞击着我的腰和腿,有的地方被冰块锋利的棱角撞伤了,渗出了血,但一点感觉也没有。再后来,连牙疼的感觉也没有了,身体仿佛已离我而去,脚变成了鱼尾巴,似乎可以在水里自如地摆动。头脑里也轻飘飘的,好像里面只有云彩,身体一下很轻,像是成了神仙似的。”
老丁自己把那次经历概括为“一趟三难”。躲过了两难,第三难又来了。他们被泥石流困在了“死人沟”里。
车在“死人沟”抛锚是最倒霉,也是最危险的。这一带环境特别恶劣,一旦滞留于此,便极其危险。
在泥石流中刨了半天车,大家弄得如泥人一般,也没把车弄出来。夜幕降临,风如狼嗥,寒气逼人。老丁只好带着大家退到避风处,等待救援。
这一等就是三天三夜。
车上的干粮吃光了,就剩下驾驶员带给别人的几斤干辣椒,也只好拿出来分着吃。
辣椒很快吃光了,但救援队还没到。饥寒交迫,再加上高原反应,每个人都痛苦不堪。
坚持到第7天早晨,好多人已写了遗书,救援的车队终于赶来了。
老丁告诉我:“那时在阿里,活过来是一种幸运。如果真的死去,也无悔无憾。我老丁只是一个普通的阿里军人。前有古人,后有来者,我不是第一个,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。”
采访结束,他给我们唱了一首他在阿里底雅乡听到过的民歌。歌词优美、简洁,内涵却深刻、博大:
天地来之不易,
就在此地来之;
寻找处处曲径,
永远吉祥如意。
他哼着这歌,显得沉醉,像是重新回到了阿里,回到了世界屋脊。
作家小记
卢一萍 1972年10月生,四川南江人。1990年3月入伍,历任战士、边防排长、干事、文艺创作员,2016年退役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白山》,小说集《帕米尔情歌》《天堂湾》《父亲的荒原》《名叫月光的骏马》《无名之地》,长篇纪实文学《八千湘女上天山》《祭奠阿里》等30余部。作品曾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解放军文艺奖、中国出版政府奖等。(卢一萍)
关键词: